

2021年5月1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元化讲堂·重读鲁迅”系列讲座第四场以线上会议形式展开。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老师主讲。郜老师从鲁迅译介的视角出发,与我系罗岗老师、孙尧天老师一起,研讨了鲁迅译介与《野草》的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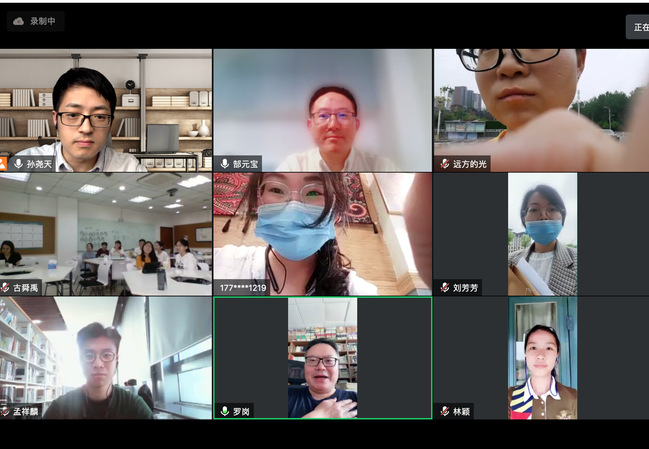
郜老师首先指出时下鲁迅研究遇到的诸多瓶颈,他认为许多年轻学者所选择的跨文化、跨语言的角度或许是最值得期待的,他今天的讲座就尝试从鲁迅译介这一跨文化跨语言的角度出发,聚焦于鲁迅个人的译介与《野草》的互文关系。
郜老师之处,在鲁迅创作《野草》之前、之中、之后,涉及三组潜文本,即广义的鲁迅本人创作、鲁迅所译介和鲁迅引用他人所译介、鲁迅或明或暗引用的他人创作。这三组潜文本同时融入《野草》的创作,构成巨大的“互文”。
具体借助互文理论来阐释《野草》时,郜老师先着眼于《野草》的得名问题,他认为有关《野草》得名的由来,有两条线索最值得重视,一是日本学者秋吉收提出的“刺成仿吾说”,另一个就是鲁迅本人在《野草·一觉》已经明确透露的来自托尔斯泰《哈泽·穆拉特》或托尔斯泰日记的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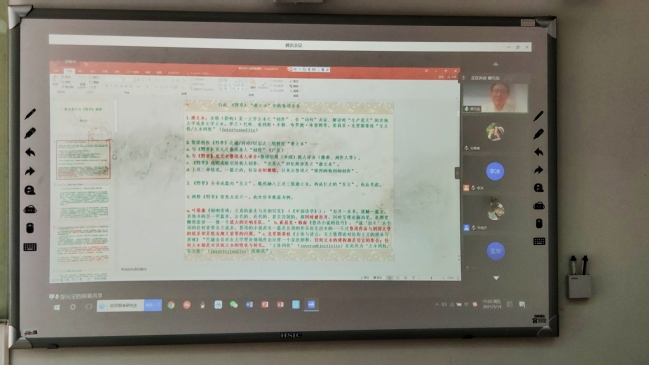
郜老师强调,对照鲁迅译介与《野草》创作,必须落实到具体篇章与词句。他从这个角度,详细论述了鲁迅所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与《野草》的密切联系。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获得并翻译此书的德文版,并且在翻译之时和之后的许多文章、讲演、谈话中予以大量引述,毫不讳言《工人绥惠略夫》对他的思想转变的影响。鲁迅对绥惠略夫的悲惨结局、革命知识分子的曲折道路、绝望之后对社会进行报复性和破坏性复仇----等等,都进行了具体分析,或者表示同情,或者不以为然,并且希望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加以警惕。顺着鲁迅译介《工人绥惠略夫》的这一思想脉络,郜老师就《野草·题辞》、《影的告别》、《墓碣文》中的“朽腐”、“将来的黄金世界”、“死尸”、“创痛酷烈”等词语和意象与《工人绥惠略夫》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郜老师还以《记谈话》《娜拉走后怎样》《头发的故事》等为有力的旁证,指出《野草》诸篇所受《工人绥惠略夫》的影响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郜老师认为,鲁迅翻译的《小约翰》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朝花夕拾》,也和《野草》具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互文关系。郜老师先从鲁迅书信对翻译《小约翰》的重视、《小约翰》译序所提及的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起信三书”的悬案以及《小约翰》译本署名问题出发,阐明《小约翰》的翻译对鲁迅的重大意义。接着郜老师针对《野草》反复出现的“梦”、“野兽”、“奇怪而高的天空”、“游魂”、“大欢喜”等词句和意象与鲁迅所译《小约翰》的关系,参照鲁迅所据的《小约翰》德文译本、英译本、华裔荷兰学者欧阳竹立根据荷兰文原本所作的中文翻译的异同,深入探索了鲁迅在翻译这些具体词句和意象时的苦心经营。

论到鲁迅研究向来看重的名篇《影的告别》,郜老师首先回顾了鲁研史上对“形影问答”来源的几种解释,特别是王瑶先生的“陶渊明《形影神》说”和张洁宇教授的“佐藤春夫《形影问答》说”,接着给出自己的解释。郜老师认为这种问答形式的灵感可能更直接地来自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构思中“自心的交争”,即形和影乃是分化出来的主体的两个面相。此外,“影”(灵魂)与“形”(肉身)的分离与对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鲁迅1918年和1920年先后以文言和白话两次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这主要指向了周氏兄弟对尼采“忠于地”思想的同情——他们都反对柏拉图以来脱离土地与身体的悬空的观念论,而将这些悬空的观念和情绪归入尼采所说的“人的碎片”、应该被超越的“人”的“游魂”。
郜老师强调,如果以鲁迅思想中的尼采和阿尔志跋涉夫的底色去重新观照《影的告别》这篇经典文本,也许会有新的收获。既然影和形是处于“自心的交争”的主体的两面,我们在解读时就应该把滔滔不绝的“影”(灵魂/“游魂”)的态度和始终沉默不语的肉体的态度放在一起来考量,不能偏于一端,不加反思地站在影的一面。但肉体的态度,或者鲁迅对肉体的设想,需要借助鲁迅杂文(比如写于1925年的《杂感》)与《影的告别》的互文关系来探索。
这样的分析方法也是从鲁迅研究的传统中继承的。郜老师提到汪晖《反抗绝望》对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之矛盾性的阐发,以及严家炎先生对于鲁迅的“复调小说”的研究,认为鲁迅小说创作中这一普遍的现象(无论叙述者的多重主体还是小说人物关系的特殊设计,比如《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中A与B的对话),诸如此类多声部的存在都要求读者不能盲目地听从某种单一的声音。即使在《野草》这部鲁迅“自己的哲学”中,也要更多地去关注被隐含(因而也长期被忽略)的其他的声音与态度。
郜老师认为,尽管《求乞者》中“求乞”、“布施”、“不布施”、“无布施心”等关键词也能在佛典(比如《金刚经》)中找到出处,但正如《小约翰》的翻译中也会出现佛典中的“大欢喜”一样,《求乞者》的这些与佛典有关的关键词的思想渊源未必就是佛典。这一点,只要同时看到鲁迅大量杂文以及《求乞者》跟鲁迅1920年重译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共同的互文关系,就可以推断。
在裴多菲与鲁迅的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望》一篇的转化创新。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早已论述过从“绝望和希望一样都是空虚的”(英文直译)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是鲁迅式的话语生成的过程,而中国学者兴万生先生《鲁迅著作中引用裴多菲诗文新考》也很重要,都可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希望》的可贵借鉴。
鲁迅“复仇”的内涵是什么?仅仅是“一个也不饶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如何理解这种单一的“复仇”与《复仇》和《复仇其二》的另一种被大大改写的“复仇”的矛盾关系?郜老师指出,从鲁迅到张承志,中国现当代文学里面并非仅有压迫/反抗、伤害/报复式的单向反应的复仇,还有同样值得重视的《野草》两篇《复仇》所展示的另一种被改写的“复仇”思想。这种“复仇”思想不仅来自鲁迅与《圣经》的对话,也来自鲁迅对绥惠略夫“一切仇仇”的单纯报复性和破坏性的复仇行为的批判性反思。
郜老师对《颓败线的颤动》的新解有两个方面,一是源于阿尔志跋涉夫创作中的“肉的气息”,即开头对老妇人年轻时卖淫场面的描写,由“欢欣而颤动”引申到鲁迅创作中对弱者似乎不应有的性欲的捕捉;其二是这一篇的“文不对题”:鲁迅在标题上有“颓败线”,正文却并未出现“颓败线”予以呼应。这在《工人绥惠略夫》中或许能找到参照系。这篇小说中有房东女儿为生计所迫嫁给粗鲁商人的情节,绥惠略夫在指责女子的情人(大学生亚拉借夫)时,使用了“屈辱”与“喜悦”这组看似矛盾的词语和等于嫖客的新郎的“凶暴淫纵的肉块”,这和鲁迅笔下的情景和用笔都高度相似。另一方面,阿尔志跋绥夫具体地写到“颓败的筋肉线”,或许就是鲁迅在标题上所使用的“颓败线”一语的由来。郜先生认为这是鲁迅的写作与《工人绥惠略夫》翻译活动之间一种莫名的纠缠互渗,是一种特别的互文关系,类似《秋夜》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与后来才完成翻译的《小约翰》的互文关系。
“游魂化蛇”在古今中外文学“灵魂出窍、化为异物”系列中不算罕见,“剖腹观心”在中国文学中也屡见不鲜,包括比干传说、《封神演义》和《水浒传》等。但鲁迅从他人之心不可知翻转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这在郜老师看来还是“难觅前驱”。他认为这一翻转的外国文学助力,主要是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的《谩》。在史福兴先生《<野草>与安德烈耶夫》的启发下,郜老师细读《谩》译文全篇,摘出几段重要译文,指出离“谩”求“诚”与《墓碣文》中求人心之“本味”以及《谩》中“谩”化为“巴蛇”并能“啮”人之心的构思,都非常接近。鲁迅让尼采《序言》中的“游魂”直接“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这大概是尼采与安特莱夫对鲁迅的交替影响吧。
郜老师的演讲之后,我系孙尧天老师做了总结,他讲到郜元宝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从鲁迅翻译来寻找鲁迅以《野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的灵感,同时他借用鲁迅“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八个字表达自己听完讲座后的感想,也表达了对郜老师后续文章的期待。
孙尧天老师邀请罗岗老师对郜元宝老师的演讲做出回应。与谈人罗岗老师指出郜老师和吴晓东老师的讲座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郜老师更加注重对文本的深入解读。罗老师指出鲁迅研究往往倾向于用已有的理论话语解释鲁迅文本,这是一种“六经注我”的行为,解读者的形象非常明显,甚至掩盖了鲁迅形象。郜老师关心的是鲁迅译介和《野草》的关系,这是一种跨语境的研究,对鲁迅译介和野草的互文关系的理解更加深入。罗岗老师也提出自己的疑虑,即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话语后来进入了鲁迅的作品中,这些话语的含义和他们的原意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针对罗老师提出的疑虑,郜老师认为,仅仅执着于对个别用法的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对野草文本和思想进行整体性分析。语词意象的借用古已有之,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
在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郜老师对“元化班”学生刘天宇提出的林纾翻译斯宾塞《仙后》和鲁迅“抉心自食”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一观点十分赞赏,称其为“今天讲座的重大收获”。
撰稿:茅嘉琪、钟雨辰、姚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