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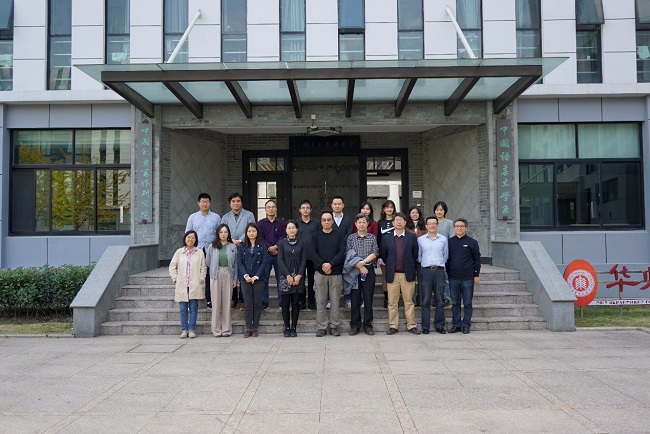
2020年11月7日上午,“文艺理论中的新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工作坊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255顺利举行。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汤拥华老师主持了本场工作坊,浙江大学徐亮老师、复旦大学张宝贵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王峰老师、浙江工商大学张瑜老师、福建省社科院王伟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安静老师、南开大学林云柯老师、南开大学李素军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张巧老师、温州大学黄家光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梁心怡博士、清华大学章含舟博士、中山大学赖锐博士等出席了本次工作坊。汤拥华老师致开幕词并表达了对各位学者的欢迎。

在工作坊的第一部分“罗蒂的遗产”这一主题中,徐亮老师《伦理的阈值与文学的效用——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案的理论基础》一文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方案的理论基础做了详细阐释,从伦理的阈值和文学的效用两方面切入,指出,罗蒂关于现代富裕社会中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共存的方案存在着很强的理论诉求与其理论基础缺乏检讨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其在伦理建构和文学效用等方面一些相互龃龉的立场。

王伟老师的《新实用主义的美育观——舒斯特曼与罗蒂比较论》一文指出舒斯特曼对罗蒂多有一些不实之指责,譬如,将美学限定于私人领域、把艺术简化为制造道德工具的诗学等等,但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两人都在反对形而上学之后致力于建构,都特别强调美育对促进社会团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不同者,关键是由美育通向共同体团结的路径:舒斯特曼强调非语言的经验,高度凸显了身体美育与大众审美的功用;罗蒂则看重语言,诉诸诗化的文化。

章含舟博士的《论同情、移情与道德进步——对罗蒂文化观的一个反思》一文提出对罗蒂而言,道德进步是一项增进敏感性的事业,罗蒂强调了其所谓的“同情心教育”理念。然而罗蒂的概念区分是相对粗糙的,他并没有意识到“移情”与“同情”之间的种类差异,这就致使其理论不仅存在着概念层次的混淆,还还无法解决衍生出的“过度/错误同情”问题。章含舟认为应当注意到,移情是同情的概念基础,前者既能“引起”后者,两者之间亦存在着紧密的“形而上学”关联。罗蒂若想证成其文化观,就必须将道德进步扎根于移情而非同情之上。

汤拥华老师在《罗蒂的遗产:讣文、预言与绝笔》一文中对罗蒂受到的赞誉与批驳进行了梳理,汤拥华老师认为,有关宗教、哲学与文学的纠结若不能解开,所谓罗蒂的遗产,便依旧扑朔迷离。罗蒂对于文学最重要的期许最后寄托于诗,之所以需要文学,不是单纯追求审美享受,也不是要从文学中求取可以用散文形式表达的真理,而是因为语词更为丰富的文化是更人性的文化,语词更为丰富的人是更完善的人。理解这个期许非常不容易,但只有理解了它,才算是理解了何谓罗蒂的遗产。

第一部分“罗蒂的遗产”专题分享结束之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评议。在第二部分“主体与身体”的分享与讨论中,张宝贵老师的《杜威生活美学的“迷”与“思”》一文中对理解杜威的关键概念——quality——做出了深入的阐释,在杜威看来,不只是艺术,决定生活所有一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迷”,当然他没用阿多诺的这个词(阿多诺称之为“enigmatic quality”),他用的是“特质”(quality)一词。按杜威的解释,quality本身虽然是迷,却不神秘,它就是有机体和环境交相作用的体现和反应,可以用emotion, feeling sensation等很多词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它。迷,涵盖了全部生活精神价值领域,是根源性的东西。但不能就此说杜威是个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同样重视生活之“思”。一旦对迷说话了,话语本身就成为了手段,是改善我们生活品质,取得完满终结的手段,也是防止人群迷乱,良性沟通的手段。这也是他工具主义名号的由来。

赖锐博士在《从实用到实践:身体美学的“西学”与“东渐”》一文中提出,自上世纪末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率先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以来,身体美学经历了从西到东、从实用到实践近廿载的跨越之旅——它虽一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却业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当然,身体美学在从西到东的途中,也曾发生不少流变和误读,乃至国内学者对“何为身体”“身体何以美学”等基本问题也仍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赖锐对从“西学”到“东渐”的两条基本线索进行了梳理,其一,回顾身体美学从实用主义哲学中脱胎而出、继而由经验论演变为身体论的“西学之源”,其二,对身体美学与中国当代实践美学的关系加以通盘考察。

林云柯老师在《“我思”与“解析几何”:实用主义中的主体性想象》一文中提到,由于康德把我们之于“世界”的认识权重至于“综合的完备性”之上,那么对“综合”本身的分析也理应成为重点,并且能够被置于具体的数理逻辑及几何学层面进行阐释。林云柯对弗里德曼在《几何原本》的第一个命题展开进行分析,提出这揭示了一个显然又往往被忽略的问题,即几何学先天综合的基础表现为尺规作图的呈现,继而分析至——“定义”的存废则隐含着“先验主体”与“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能否被切断的问题——由此视角就能够理解分析哲学何以会走向“可能世界语义学”。

在工作坊第三部分“分析与符号”这一专题中,安静老师在《从符号化的意向性通向艺术符号学的哲学向度:归纳认知视域下的赝品问题再探》一文中提出艺术赝品经常被论及的角度大体包括审美价值、艺术价值、艺术体制等,但关于赝品的认知问题还鲜有关注。无论是“以假乱真”还是“以假代真”,我们对赝品的认知过程存在“符号化的意向性”过程,即感性直观、形式直观以及本质直观三个阶段,最终的目的是离开艺术文本的符号构成,进入最终的“本质直观”,其间蕴含着探讨艺术符号学哲学向度的可能空间。

李素军老师在《何为审美:分析美学视野下的迪基-比尔兹利之争》一文中提出在乔治·迪基构建艺术体制论定义的过程中,门罗·比尔兹利的美学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期间二人有过大量论争。他们的论争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审美对象的分歧,亦即,如何判定一件艺术品的组成部分中哪些属于审美对象,哪些不属于,二是关于审美经验的论争。三是比尔兹利对于艺术体制论的批判。

黄家光老师在《语言实用主义美学的世界之维——论古德曼的艺术语言》一文中指出语言实用主义美学在与身体实用主义美学的论战中显现出理论生命力。但罗蒂的语言实用主义美学方案有语言唯心论的困难。古德曼对“艺术语言”的探究所提供的“非实在论”,为我们在语言实用主义美学框架内提供了重新谈论世界的契机。以“指称”概念为中心重构古德曼的“艺术语言”理论,围绕样式与世界关系问题(语言构造世界),回应舍夫勒等人对古德曼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比较罗蒂与古德曼之异同。古德曼通过康德式的语言构造世界的方案,将世界纳入语言之中。这个方案一定程度上弥补上罗蒂在此问题上的不足,为我们展示了语言实用主义美学的世界之维。

在本部分结束后大家也进行了热烈的评议与讨论。在本次工作坊的第四部分“理论与未来”这一部分,张巧老师在《戴维森与实用主义文论的对话与交锋》一文中指出戴维森的实用主义面孔主要是通过罗蒂的阐发进入学界视野的。一方面,罗蒂引入戴维森的整体论原则和对基要主义的批判加强了其新实用主义文论的建设,这可以视为戴维森思想和新实用主义文论对话的切面;另一方面,戴维森本人的意图论却和新实用主义文论的多元阐释主义之间产生张力,戴维森的反约定论也必定指向对“阐释共同体”的批判。张巧在文中将戴维森作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文论的调节性工具,并展示了戴维森可能通往实用主义的另一条路径。

梁心怡博士在《作为伦理行动的“模仿”——R.S.克兰诗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一文中提出,作为芝加哥文学批评派的领军人物,R.S.克兰最富争议的事业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研究与复兴。这不仅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也与克兰本人对多元论的提倡看似矛盾。但是,克兰所谓多元论之优越性,是来自于它的工具价值,而非内在价值。批评多元论意味着不同的批评理论按照各自的问题框架,有限地处理特定的文本问题。在克兰看来,诗学是一种更接近于伦理学的实践科学,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模仿的”伦理行动。这是克兰的伦理批评与布斯以修辞为核心的伦理批评的主要区别所在。

张瑜老师在《可能世界的文学传统与发展未来》一文中提到,对于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注最初源于对文学语言研究现状的不满。话语产生的效果是无法概括也无法预料的,这种意义的无限延伸现象便与“可能世界”有关,也就是语言在创造和构建着一个可能世界。关于可能世界的文学传统,最初源于两希文明,之后莱布尼茨提出了关于可能世界的神学理论,并由其思想继承者沃尔夫引入到文学和艺术的研究领域,此后18世纪又由鲍姆加登等人将可能世界理论发展至高峰。关于可能世界的发展未来,张瑜老师关注了中国的“境界”与西方的“可能世界”二者之间的联系,探讨了在世界平台上研究文学理论的内在沟通问题。“可能世界”的未来问题也与其在文学理论运用中的三种形态有关,即作为审美对象、作为语言的性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最后张瑜老师表示每一种理论其实都是一种可能性的图景,理论之间远远不是一种取代关系。
在各位老师发言结束后,王峰老师对本次工作坊进行总结致辞,他认为本次工作坊的主题限定使得对新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阐发做到了很深入的程度,他对相关研究的未来前景充满期待。

一天的会议内容充实,话题集中,信息丰富,讲者评者无不全情投入,无论是与会代表还是旁听的学生都感觉收获满满,本次工作坊在融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撰稿|孙琪琪
排版|林聪




